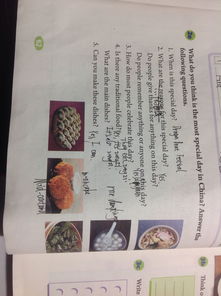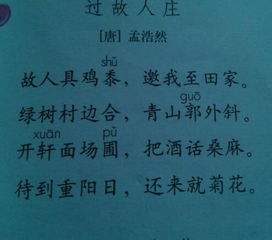孙志刚事件谁报案(天河公安局主要领导)
- 明星八卦
- 2022-12-27 20:54:17
- -
2003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后,各地的收容遣送站撤牌。 资料图
孙志刚的死,为收容制度的废除鸣响了最后一枪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15年前的6月,施行21年的“收容法”被废止。
这是一次由政府亲自操刀的手术,旧法中所有备受争议的强制性内容和字句被全部删除——从破旧到立新,为时不到5天。
而推动这一极速变化的,是2003年3月因为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而被关进收容所,导致死亡的孙志刚。
在孙志刚事件中,从律师的取证到独立的法医鉴定,再到公民上书,最后收容审查制度被废止。
孙志刚之死
当时上书中央的五位法学家之一、如今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在十几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时,依然激动不已。
沈岿从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做短期访问研究回国之后的那段时间,除了SARS肆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外,他记得的一个人的名字就是孙志刚。
2003年3月17日晚10点,刚刚大学毕业两年的青年孙志刚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因为刚来广州,孙志刚还没办理暂住证,当晚他出门时,也没随身携带身份证。当晚11点左右,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
随后,孙志刚被错误地作为“三无”人员送至广州天河区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由于待遣所民警的不负责任,导致孙志刚“被错误地作为被收容遣送人员送至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
9个小时后,孙志刚向中转站报告自己有心脏病,因为紧张而心慌、失眠,要求放他出去或住院治疗。中转站遂以“心动过速待查”为由,将孙送往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
在这里,孙志刚23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3月20日凌晨,在遭同病房的8名被收治人员两度轮番殴打之后,孙志刚不治身亡。
从后来的尸检结果看,孙志刚死前几天内被人殴打并最终导致死亡已是不争的事实。
孙志刚该被收容吗?一个公民,有工作单位,有正常居所,有身份证,只因为缺一张暂住证,被收容,被遣送,乃至最后失去了生命。
实际上,在孙志刚案件发生之前,因收容制度而被强奸的女子,失踪的孩子,莫名死亡的打工者,年年都见诸报端。
孙志刚的死,为收容制度的废除鸣响了最后一枪。
收容伊始
实际上,收容制度的出台和当时的社会形势不无关系。
1961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决定在大中城市设立“收容遣送站”,以民政部门为主,负责将“盲流”收容起来并遣送原籍。
这是收容制度的发端,针对控制因“三年自然灾害”而进城的农民。
“(上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刚刚开始,一部分农民开始背井离乡进城谋生。当时国家户籍制度还相当严格,但从那时候开始,一过春节,火车站已经挤满了背着沉甸甸包裹进城的农民。‘盲流’的提法这样才有的。”研究收容制和中国户籍制度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说。
对于刚刚经历“自然灾害”的政府而言,农民大量弃田务工对农业经济的负面作用是致命的。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文革”期间,因为户籍制度强化对城市人口的严格控制,盲流人口不多,主要是少量的乞讨者,这期间的公检法加强了对这部分人员的执法力度,盲流人口变成被管制对象。
事实上,尽管当时的政府严格以户籍制度控制城市人口,不仅严控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而且通过“上山下乡”等手段使城市青年流向农村,以减低城市就业的压力。“盲流”人口因此得到严格控制,但并未绝止,所以收容遣返政策一直在严厉执行。
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工业化进程日益扩大了城乡差距,给人口流动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经济驱动力,使农村人口涌向城市的潮流再也无法控制。
于是,上世纪60年代曾一度试行的“收容遣送”便在这种前提下成为管理者的首选。
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收容遣送”的正式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收容制度由此全面启动。
在收容遣送条例的开篇有这样的表述:“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特制定本办法。”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显然后一句话才是关键所在。在城乡博弈中,其初衷首先是维护城市秩序,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问题。收容遣送制度是偏向城市安全的”。
马怀德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从一开始的确存在明显的问题,“对待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差别立法,首先就违背了法的基本精神。其次,强制力的介入时刻存在着侵犯个人权利的可能”。
至于城市之所以在处理流动人口问题上采取这种明显具有“超法律”手段的深层原因,顾骏分析说:“城市是一个权利体系。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城市权利资源发生了大规模重新配置,权利资源短缺成为一段时间内的普遍现象。当城市原有人口在权利资源上发生争夺的情况下,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很难指望获得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份额。所谓‘城市是谁的’这一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村人口在城市中的权利缺乏问题。”
事实上,收容遣送制度也确实在近十年间给城市控制人口过快膨胀、改善治安环境带来过显著成效。来自公安部的资料显示,“犯罪率在上世纪90年代初达到最高峰后,开始有回落趋势,1995年的大小刑事案件数目比1991年减少了13351起”。
其中收容制度功不可没。但顾骏认为,城市对于“收容遣送”在40年间产生了严重的“整体性依赖”,就像“吗啡针”,“镇痛就得加大剂量”。
矛盾初现
1991年,“民工潮”泛滥,各大城市不堪重负。
国务院于是发出第48号文件,将收容对象扩大到“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三无”人员。在现实执行中,“三无”往往变成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三证”缺一不可。
其后几年,民政部、公安部数次联合发文,进一步强化收容遣送工作,收容遣送成为公安、民政、街道的重要工作。而收容制度的功能也从最初维护城市形象、维护城市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演变为配合打击刑事犯罪的一项措施。
当时民政部的数据显示,北京市在1999年的遣返人数不足15万人,到2000年上半年,收容遣返人数就达到18万,超出1999年全年总和,2001年,2002年到2003年上半年,每年增加超过20个百分点。
当时有政协委员做了这样一项抽样调查,在抽样的10起农民工被收容案例中,几乎没有依法执行的,而问题就出在大量超范围收容上。据估计,在收容人员中,真正属于救助对象的不到15%,其余大部分是“三无人员”。
随着民工在城市里的人口日益增多,遣送量每年急速增长。基层执行人员的权力被放大,收容遣送制度甚至成为一些地方单位的创收项目。违法滥用权力的事件于是屡有发生,相关立法质疑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沈岿看来,收容制度自身就包含着反规范、反权利的成分,在实际运作中,部门利益、部分执法者素质等因素加进来,制度本身包含的反规范方面恶性膨胀便不可避免。
沈岿认为,收容遣送制度在三个层面上纵容了各种恶性事件的产生:
一是多种功能赋予了这个制度,导致这一制度的变形甚至变异,一些地方政府可以毫无理由将“三无人员”赶走,还可以当面把你的证件撕掉,让你回去。其二,这里面可能有经济因素,使这种制度依然存在,制度的设计者可能没有想到,但是它确实成为了一种创收工具。第三,“在我们国家各种涉及强制措施的制度中可能存在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暴力会出现,失控的制度会将它释放出来”。
这样关于收容制度的立废之争几乎持续了整整40年。
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废止收容制度的呼声就没有停过。有法学界人士透露,每年全国人大都会收到上千封要求废止“收容法”的上书。
顾骏认为,针对流动人口的收容遣送已经在多个层面上与城市管理体制乃至城市生活本身发生交互作用,40年深刻依附于我们城市化的体制之中,“废止当然不是轻易之举”。
上书中央
如果没有“三博士”和“五学者”的上书,孙志刚也许不会是最后一个死在收容所的中国人。
2003年5月14日,3名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建议改变或撤销收容遣送制度。
和一般的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制定、修改法律的建议不同,这份公民建议书非同寻常之处在于,是公民依照立法法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有关法规进行违宪审查的创举。
这份公民建议书,以民间形式启动了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违宪审查权的程序,罕有先例。
9天后,33岁的沈岿作为执笔人,跟其他4名学者一起,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建议:就孙志刚事件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建议全国人大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
沈岿向法治周末记者回忆,他们这么做,首先是为了支援三博士的行为。而“五学者”呼应“三博士”,给予了舆论上的支持。
沈岿并没有想到,上书在一个月之后就有了结果。
2003年6月2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了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沈岿认为,决策层反应迅速的原因是中央当时就有对旧制度进行改革的想法,而且在人口流动率升高的大时代背景之下,收容遣送这种人口管制措施已经不适应深入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此外,民意压力亦是一大促进因素。
尽管沈岿他们的建议没有得到完全采纳,但他依然很高兴,这一事件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是2000年立法法通过后,公民用违宪审查建议权获得成功的第一个事例。”沈岿说。
这样的结果给沈岿很大的信心:如果有心使用立法法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沈岿看来,近十几年来让他觉得“最美好的事就是孙志刚事件后,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
“从这件事上,能切实感受到中国的法治建设在进步。”沈岿说。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6月5日至6月6日公开审理乔燕琴、李海婴、钟辽国等故意伤害原广州市达奇服装公司职员孙志刚致死案,于9日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乔燕琴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李海婴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钟辽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周利伟、张明君、吕二鹏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被告人李龙生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判处被告人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乔志军、胡金艳有期徒刑3年至10年。
同日,孙志刚案涉及的原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原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原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负责人彭红军,医生任浩强,护士邹丽萍、曾伟林等6人,以玩忽职守罪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和白云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年至3年。
案情回放
3月17日晚,27岁的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外出,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错误收容。3月18日晚,孙志刚称有心脏病被送至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3月19日晚,因孙志刚大声呼叫,引起救治站护工乔燕琴不满。乔遂与吕二鹏、乔志军、胡金艳等人商量,授意李海婴等8名被收治人员殴打孙志刚。3月20日凌晨,李海婴、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等先后两度对孙志刚轮番殴打,致使孙志刚于3月20日上午经抢救无效死亡。后经法医鉴定,孙志刚系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判决依据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乔燕琴、李海婴、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吕二鹏、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乔志军、胡金艳共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致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惩处。其中,乔燕琴指使、纠合其他被告人对孙志刚实施伤害行为,系本案主犯,应予从严惩处;李海婴、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吕二鹏等两度轮番殴打致死被害人,罪行严重,应从重处罚;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乔志军、胡金艳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次要作用,是从犯,应依法惩处。但鉴于李文星在犯罪时未满18周岁,依法从轻处罚。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和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原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原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原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负责人彭红军,医生任浩强,护士邹丽萍、曾伟林等6人,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受国家机关委托行使公务的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义务,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孙志刚被错误收容并在救治站遭受伤害致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玩忽职守 孙志刚事件是指媒体发挥舆论监督功能,通过新闻报道披露政府执法机关收容拘禁公民孙志刚而致其被殴而死这一事件,推动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条例,是保护公民权利的著名案例。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 孙志刚事件是指媒体发挥舆论监督功能,通过新闻报道披露政府执法机关收容拘禁公民孙志刚而至其被殴打而死这一事件,推动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条例,是保护公民权利的著名案例。
孙志刚的死,为收容制度的废除鸣响了最后一枪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15年前的6月,施行21年的“收容法”被废止。
这是一次由政府亲自操刀的手术,旧法中所有备受争议的强制性内容和字句被全部删除——从破旧到立新,为时不到5天。
而推动这一极速变化的,是2003年3月因为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而被关进收容所,导致死亡的孙志刚。
在孙志刚事件中,从律师的取证到独立的法医鉴定,再到公民上书,最后收容审查制度被废止。
孙志刚之死
当时上书中央的五位法学家之一、如今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在十几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时,依然激动不已。
沈岿从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做短期访问研究回国之后的那段时间,除了SARS肆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外,他记得的一个人的名字就是孙志刚。
2003年3月17日晚10点,刚刚大学毕业两年的青年孙志刚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因为刚来广州,孙志刚还没办理暂住证,当晚他出门时,也没随身携带身份证。当晚11点左右,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
随后,孙志刚被错误地作为“三无”人员送至广州天河区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由于待遣所民警的不负责任,导致孙志刚“被错误地作为被收容遣送人员送至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
9个小时后,孙志刚向中转站报告自己有心脏病,因为紧张而心慌、失眠,要求放他出去或住院治疗。中转站遂以“心动过速待查”为由,将孙送往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
在这里,孙志刚23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3月20日凌晨,在遭同病房的8名被收治人员两度轮番殴打之后,孙志刚不治身亡。
从后来的尸检结果看,孙志刚死前几天内被人殴打并最终导致死亡已是不争的事实。
孙志刚该被收容吗?一个公民,有工作单位,有正常居所,有身份证,只因为缺一张暂住证,被收容,被遣送,乃至最后失去了生命。
实际上,在孙志刚案件发生之前,因收容制度而被强奸的女子,失踪的孩子,莫名死亡的打工者,年年都见诸报端。
孙志刚的死,为收容制度的废除鸣响了最后一枪。
收容伊始
实际上,收容制度的出台和当时的社会形势不无关系。
1961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决定在大中城市设立“收容遣送站”,以民政部门为主,负责将“盲流”收容起来并遣送原籍。
这是收容制度的发端,针对控制因“三年自然灾害”而进城的农民。
“(上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刚刚开始,一部分农民开始背井离乡进城谋生。当时国家户籍制度还相当严格,但从那时候开始,一过春节,火车站已经挤满了背着沉甸甸包裹进城的农民。‘盲流’的提法这样才有的。”研究收容制和中国户籍制度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说。
对于刚刚经历“自然灾害”的政府而言,农民大量弃田务工对农业经济的负面作用是致命的。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文革”期间,因为户籍制度强化对城市人口的严格控制,盲流人口不多,主要是少量的乞讨者,这期间的公检法加强了对这部分人员的执法力度,盲流人口变成被管制对象。
事实上,尽管当时的政府严格以户籍制度控制城市人口,不仅严控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而且通过“上山下乡”等手段使城市青年流向农村,以减低城市就业的压力。“盲流”人口因此得到严格控制,但并未绝止,所以收容遣返政策一直在严厉执行。
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工业化进程日益扩大了城乡差距,给人口流动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经济驱动力,使农村人口涌向城市的潮流再也无法控制。
于是,上世纪60年代曾一度试行的“收容遣送”便在这种前提下成为管理者的首选。
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收容遣送”的正式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收容制度由此全面启动。
在收容遣送条例的开篇有这样的表述:“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特制定本办法。”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显然后一句话才是关键所在。在城乡博弈中,其初衷首先是维护城市秩序,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问题。收容遣送制度是偏向城市安全的”。
马怀德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从一开始的确存在明显的问题,“对待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差别立法,首先就违背了法的基本精神。其次,强制力的介入时刻存在着侵犯个人权利的可能”。
至于城市之所以在处理流动人口问题上采取这种明显具有“超法律”手段的深层原因,顾骏分析说:“城市是一个权利体系。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城市权利资源发生了大规模重新配置,权利资源短缺成为一段时间内的普遍现象。当城市原有人口在权利资源上发生争夺的情况下,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很难指望获得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份额。所谓‘城市是谁的’这一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村人口在城市中的权利缺乏问题。”
事实上,收容遣送制度也确实在近十年间给城市控制人口过快膨胀、改善治安环境带来过显著成效。来自公安部的资料显示,“犯罪率在上世纪90年代初达到最高峰后,开始有回落趋势,1995年的大小刑事案件数目比1991年减少了13351起”。
其中收容制度功不可没。但顾骏认为,城市对于“收容遣送”在40年间产生了严重的“整体性依赖”,就像“吗啡针”,“镇痛就得加大剂量”。
矛盾初现
1991年,“民工潮”泛滥,各大城市不堪重负。
国务院于是发出第48号文件,将收容对象扩大到“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三无”人员。在现实执行中,“三无”往往变成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三证”缺一不可。
其后几年,民政部、公安部数次联合发文,进一步强化收容遣送工作,收容遣送成为公安、民政、街道的重要工作。而收容制度的功能也从最初维护城市形象、维护城市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演变为配合打击刑事犯罪的一项措施。
当时民政部的数据显示,北京市在1999年的遣返人数不足15万人,到2000年上半年,收容遣返人数就达到18万,超出1999年全年总和,2001年,2002年到2003年上半年,每年增加超过20个百分点。
当时有政协委员做了这样一项抽样调查,在抽样的10起农民工被收容案例中,几乎没有依法执行的,而问题就出在大量超范围收容上。据估计,在收容人员中,真正属于救助对象的不到15%,其余大部分是“三无人员”。
随着民工在城市里的人口日益增多,遣送量每年急速增长。基层执行人员的权力被放大,收容遣送制度甚至成为一些地方单位的创收项目。违法滥用权力的事件于是屡有发生,相关立法质疑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沈岿看来,收容制度自身就包含着反规范、反权利的成分,在实际运作中,部门利益、部分执法者素质等因素加进来,制度本身包含的反规范方面恶性膨胀便不可避免。
沈岿认为,收容遣送制度在三个层面上纵容了各种恶性事件的产生:
一是多种功能赋予了这个制度,导致这一制度的变形甚至变异,一些地方政府可以毫无理由将“三无人员”赶走,还可以当面把你的证件撕掉,让你回去。其二,这里面可能有经济因素,使这种制度依然存在,制度的设计者可能没有想到,但是它确实成为了一种创收工具。第三,“在我们国家各种涉及强制措施的制度中可能存在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暴力会出现,失控的制度会将它释放出来”。
这样关于收容制度的立废之争几乎持续了整整40年。
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废止收容制度的呼声就没有停过。有法学界人士透露,每年全国人大都会收到上千封要求废止“收容法”的上书。
顾骏认为,针对流动人口的收容遣送已经在多个层面上与城市管理体制乃至城市生活本身发生交互作用,40年深刻依附于我们城市化的体制之中,“废止当然不是轻易之举”。
上书中央
如果没有“三博士”和“五学者”的上书,孙志刚也许不会是最后一个死在收容所的中国人。
2003年5月14日,3名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建议改变或撤销收容遣送制度。
和一般的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制定、修改法律的建议不同,这份公民建议书非同寻常之处在于,是公民依照立法法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有关法规进行违宪审查的创举。
这份公民建议书,以民间形式启动了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违宪审查权的程序,罕有先例。
9天后,33岁的沈岿作为执笔人,跟其他4名学者一起,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建议:就孙志刚事件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建议全国人大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
沈岿向法治周末记者回忆,他们这么做,首先是为了支援三博士的行为。而“五学者”呼应“三博士”,给予了舆论上的支持。
沈岿并没有想到,上书在一个月之后就有了结果。
2003年6月2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了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沈岿认为,决策层反应迅速的原因是中央当时就有对旧制度进行改革的想法,而且在人口流动率升高的大时代背景之下,收容遣送这种人口管制措施已经不适应深入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此外,民意压力亦是一大促进因素。
尽管沈岿他们的建议没有得到完全采纳,但他依然很高兴,这一事件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是2000年立法法通过后,公民用违宪审查建议权获得成功的第一个事例。”沈岿说。
这样的结果给沈岿很大的信心:如果有心使用立法法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沈岿看来,近十几年来让他觉得“最美好的事就是孙志刚事件后,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
“从这件事上,能切实感受到中国的法治建设在进步。”沈岿说。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6月5日至6月6日公开审理乔燕琴、李海婴、钟辽国等故意伤害原广州市达奇服装公司职员孙志刚致死案,于9日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乔燕琴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李海婴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钟辽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周利伟、张明君、吕二鹏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被告人李龙生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判处被告人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乔志军、胡金艳有期徒刑3年至10年。
同日,孙志刚案涉及的原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原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原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负责人彭红军,医生任浩强,护士邹丽萍、曾伟林等6人,以玩忽职守罪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和白云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年至3年。
案情回放
3月17日晚,27岁的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外出,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错误收容。3月18日晚,孙志刚称有心脏病被送至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3月19日晚,因孙志刚大声呼叫,引起救治站护工乔燕琴不满。乔遂与吕二鹏、乔志军、胡金艳等人商量,授意李海婴等8名被收治人员殴打孙志刚。3月20日凌晨,李海婴、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等先后两度对孙志刚轮番殴打,致使孙志刚于3月20日上午经抢救无效死亡。后经法医鉴定,孙志刚系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判决依据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乔燕琴、李海婴、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吕二鹏、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乔志军、胡金艳共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致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惩处。其中,乔燕琴指使、纠合其他被告人对孙志刚实施伤害行为,系本案主犯,应予从严惩处;李海婴、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吕二鹏等两度轮番殴打致死被害人,罪行严重,应从重处罚;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乔志军、胡金艳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次要作用,是从犯,应依法惩处。但鉴于李文星在犯罪时未满18周岁,依法从轻处罚。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和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原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原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原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负责人彭红军,医生任浩强,护士邹丽萍、曾伟林等6人,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受国家机关委托行使公务的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义务,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孙志刚被错误收容并在救治站遭受伤害致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玩忽职守 孙志刚事件是指媒体发挥舆论监督功能,通过新闻报道披露政府执法机关收容拘禁公民孙志刚而致其被殴而死这一事件,推动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条例,是保护公民权利的著名案例。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 孙志刚事件是指媒体发挥舆论监督功能,通过新闻报道披露政府执法机关收容拘禁公民孙志刚而至其被殴打而死这一事件,推动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条例,是保护公民权利的著名案例。
本文由作者笔名:介之桃032 于 2022-12-27 20:54:17发表在本站,原创文章,禁止转载,文章内容仅供娱乐参考,不能盲信。
本文链接:https://www.3m3q.com/mx-12290.html
 介之桃032
介之桃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