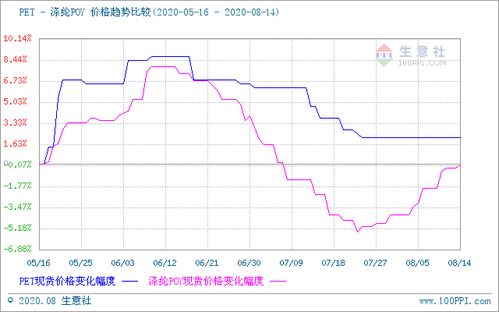乡村人物谱之一《憨 媳 妇》(善解人意漂亮的媳妇)
- 明星八卦
- 2023-03-07 21:54:01
- -
憨 媳 妇
憨者近痴,近呆,近疯,近傻;却又非痴,非呆,非疯,非傻。憨媳妇就是这么一个另类。
憨媳妇是村里有名的莽汉土墩的媳妇。前几年农家山墙上常可看到这么一条标语:不娶文盲女,不嫁文盲汉。唉,那就只好憨女嫁莽汉了吧。
说是媳妇,其实并未明媒正娶,也不存在拜天拜地,反正是土墩的亲戚的亲戚什么的不知从哪弄来这么一个女的,往这光棍房里一塞,来日再在邻里一明张,这么着,便成了一对夫妻。文明人可能把这叫非法同居,但在相对闭塞的乡村,这种现象可还普遍着呢。怎么着?不就是捉对过日子吗?
乡邻们不关心合法不合法,他们关心这土墩媳妇的其他信息,姓甚名谁呀,何方人氏呀,有何底细呀。嘿,哪怕是最喜最善猎奇的包打听也一无所获——来路不明,一问三不知,夫家人也守口如瓶。很快人们便得出一个结论:这女子其实是个“神经”,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但总不能就这么着称呼人吧,于是——也不知谁带的头,一传十,十传百,男女老少都叫她“憨媳妇”。这头衔她夫家倒是认了,至于她自己——她从来都不跟外人搭腔,叫这叫那又同她有什么相干呢?
可不要以为不搭腔就是不说话,是哑巴,那可大错而特错了。因为呀——哎呀,她实在是太能说太能说了——从早晨出门(她可总是起的很早的)到傍晚不再出门(人们也从没见过她夜晚出过门,恐怕就是发八级地震也如此吧)——我没用“一天到晚”这个词,因为一有“通宵达旦”、“没日没夜”的嫌疑,二来她白天里不知要进出过多少次门,至于进门后的情形如何,人们避之尚惟恐不及,总算讨得耳根一时清净,哪还会去关心、打听呢?——她可总是在说,说,说!老远听到叽里咕哝的,就知道是憨媳妇来啦!不用看她(确实也有很多人懒得看她),只要听到几阵嘀咕声,就可以准确无误的知道她从你身边经过了几遍。其实那种说不是说话,根本没有说话对象;也不像是自言自语,好像缺少说话的内容。那就叫嘟哝吧。嘟哝什么呢?因为本来就听不出她操的是哪门子语言,再加上完全是语无伦次,所以呀,听了多年,乡邻们也永远感到像是在听天书。不过,那嘟哝时而高昂,时而低沉,时而急促,时而舒缓,各尽变化,难以尽述。我想,即便是动物,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现喜怒哀乐的,何况是人呢?这憨媳妇是在用这种别人不胜其烦、她自己不厌其烦的嘟哝声,来宣泄她作为人的“喜怒哀乐”吧?
只不过,周围人早已见怪不怪、无动于衷罢了。好像她本来就是个与周围毫不相干的人,或者干脆不是“人”,只是个传宗接代的工具,只是个干活的机器。对她来说,残汤剩饭(没有残羹冷炙那么高级)是家常便饭,而吃什么她都有胃口,都狼吞虎咽,都津津有味。村里人都津津乐道这么一个她家里人传出的故事:有一天,她在外干活时,在河边看到一只不知被谁扔了几天的小死猪崽,早已臭气烘烘,苍蝇成群的,她偏捡了回来,煮了吃了。家里人吓得谁也不敢尝,她却吃得津津有味——只害得她婆婆亲自出马,在水塘里洗了一下午锅具,也不知是否洗净了那脏那臭那恶心的滋味。偏食?对她来说,无异于是一个外星人才有的毛病吧。至于喝,当然无福消受什么“饮料”,她只喝生水,不分好歹的喝,春夏秋冬的喝——只在生孩子时,被家里人严防死守才禁了七天。结果呢,乖乖,她可从来不生病!有句歌词叫“酒肉穿肠过”,套用在憨媳妇身上,那真叫“吃喝穿肠过”,好像与她的口味喜好呀、身体健康呀毫不相干。
憨媳妇倒也有一点让人眼红——能干,当牛做马的能干,不知当牛做马的能干!担水——从水井挑,从门塘挑,一天少说总得三四担;放牛——拉到山上,拉到河边,拉到地头,她从不与人为伍。别人是“放牛”,放牛随便吃,很轻松的照看而已;她是“牵牛”,牵出,牵吃,牵回;洗东西——衣服呀,毛巾抹布呀,各种器具呀,也不知怎么总有那么多要洗的,一趟趟的跑。有次乘凉时,有好事者数她一上午到塘里洗了六次玩意!以上只不过是随便列出的几个日常性事项。其实她的“活路”那可真是五花八门:家里的活,田地的活;女人干的活,男人干的活;你能想到的活,你做梦都想不到的活,她都在干。不仅干,而且能干。用蛇皮袋挑粪送地头,她赶两个来回,你不一定能跑一趟;栽秧季节,三两个青壮妇女暗暗同她较劲,合起来的进度赶不上她一个人的。可你知道吗?她身材瘦小,她身板单薄,绝不是那种母夜叉式的五大三粗。
我总奇怪,这杂七杂八的活她怎么都会干?是天生的吗?这是人干的不是人干的活她为什么干的出色呢?这里面有什么作为“人”的奥秘呢?憨媳妇若是科学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为什么又这么正常乃至超常呢?她为什么和我们经常见到的疯疯癫癫的“神经”不同呢?
憨媳妇的勤劳、能干是受她丈夫的影响吗?土墩虽是莽汉,倒真像有使不完的劲,是个山圪旯里的干活好把式,可是在一个早晨他一个人上完一车沙后(通常是两车)猝然而死了。不久,憨媳妇也无缘无故、毫无征兆的失踪了,后来村里再也没人见到她。我的这些疑问也就无从破解了,她这个多余人也给周围人留下一串串解不开的谜。
她还能留下什么?
她还为夫家留下她曾活过的印记——一个女儿。该有十来岁了吧,说家乡话,长得还秀气,文盲。
憨者近痴,近呆,近疯,近傻;却又非痴,非呆,非疯,非傻。憨媳妇就是这么一个另类。
憨媳妇是村里有名的莽汉土墩的媳妇。前几年农家山墙上常可看到这么一条标语:不娶文盲女,不嫁文盲汉。唉,那就只好憨女嫁莽汉了吧。
说是媳妇,其实并未明媒正娶,也不存在拜天拜地,反正是土墩的亲戚的亲戚什么的不知从哪弄来这么一个女的,往这光棍房里一塞,来日再在邻里一明张,这么着,便成了一对夫妻。文明人可能把这叫非法同居,但在相对闭塞的乡村,这种现象可还普遍着呢。怎么着?不就是捉对过日子吗?
乡邻们不关心合法不合法,他们关心这土墩媳妇的其他信息,姓甚名谁呀,何方人氏呀,有何底细呀。嘿,哪怕是最喜最善猎奇的包打听也一无所获——来路不明,一问三不知,夫家人也守口如瓶。很快人们便得出一个结论:这女子其实是个“神经”,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但总不能就这么着称呼人吧,于是——也不知谁带的头,一传十,十传百,男女老少都叫她“憨媳妇”。这头衔她夫家倒是认了,至于她自己——她从来都不跟外人搭腔,叫这叫那又同她有什么相干呢?
可不要以为不搭腔就是不说话,是哑巴,那可大错而特错了。因为呀——哎呀,她实在是太能说太能说了——从早晨出门(她可总是起的很早的)到傍晚不再出门(人们也从没见过她夜晚出过门,恐怕就是发八级地震也如此吧)——我没用“一天到晚”这个词,因为一有“通宵达旦”、“没日没夜”的嫌疑,二来她白天里不知要进出过多少次门,至于进门后的情形如何,人们避之尚惟恐不及,总算讨得耳根一时清净,哪还会去关心、打听呢?——她可总是在说,说,说!老远听到叽里咕哝的,就知道是憨媳妇来啦!不用看她(确实也有很多人懒得看她),只要听到几阵嘀咕声,就可以准确无误的知道她从你身边经过了几遍。其实那种说不是说话,根本没有说话对象;也不像是自言自语,好像缺少说话的内容。那就叫嘟哝吧。嘟哝什么呢?因为本来就听不出她操的是哪门子语言,再加上完全是语无伦次,所以呀,听了多年,乡邻们也永远感到像是在听天书。不过,那嘟哝时而高昂,时而低沉,时而急促,时而舒缓,各尽变化,难以尽述。我想,即便是动物,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现喜怒哀乐的,何况是人呢?这憨媳妇是在用这种别人不胜其烦、她自己不厌其烦的嘟哝声,来宣泄她作为人的“喜怒哀乐”吧?
只不过,周围人早已见怪不怪、无动于衷罢了。好像她本来就是个与周围毫不相干的人,或者干脆不是“人”,只是个传宗接代的工具,只是个干活的机器。对她来说,残汤剩饭(没有残羹冷炙那么高级)是家常便饭,而吃什么她都有胃口,都狼吞虎咽,都津津有味。村里人都津津乐道这么一个她家里人传出的故事:有一天,她在外干活时,在河边看到一只不知被谁扔了几天的小死猪崽,早已臭气烘烘,苍蝇成群的,她偏捡了回来,煮了吃了。家里人吓得谁也不敢尝,她却吃得津津有味——只害得她婆婆亲自出马,在水塘里洗了一下午锅具,也不知是否洗净了那脏那臭那恶心的滋味。偏食?对她来说,无异于是一个外星人才有的毛病吧。至于喝,当然无福消受什么“饮料”,她只喝生水,不分好歹的喝,春夏秋冬的喝——只在生孩子时,被家里人严防死守才禁了七天。结果呢,乖乖,她可从来不生病!有句歌词叫“酒肉穿肠过”,套用在憨媳妇身上,那真叫“吃喝穿肠过”,好像与她的口味喜好呀、身体健康呀毫不相干。
憨媳妇倒也有一点让人眼红——能干,当牛做马的能干,不知当牛做马的能干!担水——从水井挑,从门塘挑,一天少说总得三四担;放牛——拉到山上,拉到河边,拉到地头,她从不与人为伍。别人是“放牛”,放牛随便吃,很轻松的照看而已;她是“牵牛”,牵出,牵吃,牵回;洗东西——衣服呀,毛巾抹布呀,各种器具呀,也不知怎么总有那么多要洗的,一趟趟的跑。有次乘凉时,有好事者数她一上午到塘里洗了六次玩意!以上只不过是随便列出的几个日常性事项。其实她的“活路”那可真是五花八门:家里的活,田地的活;女人干的活,男人干的活;你能想到的活,你做梦都想不到的活,她都在干。不仅干,而且能干。用蛇皮袋挑粪送地头,她赶两个来回,你不一定能跑一趟;栽秧季节,三两个青壮妇女暗暗同她较劲,合起来的进度赶不上她一个人的。可你知道吗?她身材瘦小,她身板单薄,绝不是那种母夜叉式的五大三粗。
我总奇怪,这杂七杂八的活她怎么都会干?是天生的吗?这是人干的不是人干的活她为什么干的出色呢?这里面有什么作为“人”的奥秘呢?憨媳妇若是科学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为什么又这么正常乃至超常呢?她为什么和我们经常见到的疯疯癫癫的“神经”不同呢?
憨媳妇的勤劳、能干是受她丈夫的影响吗?土墩虽是莽汉,倒真像有使不完的劲,是个山圪旯里的干活好把式,可是在一个早晨他一个人上完一车沙后(通常是两车)猝然而死了。不久,憨媳妇也无缘无故、毫无征兆的失踪了,后来村里再也没人见到她。我的这些疑问也就无从破解了,她这个多余人也给周围人留下一串串解不开的谜。
她还能留下什么?
她还为夫家留下她曾活过的印记——一个女儿。该有十来岁了吧,说家乡话,长得还秀气,文盲。
本文由作者笔名:乐燕铌3Q 于 2023-03-07 21:54:01发表在本站,原创文章,禁止转载,文章内容仅供娱乐参考,不能盲信。
本文链接:https://www.3m3q.com/mx-56482.html
 乐燕铌3Q
乐燕铌3Q